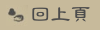|
作者姓名: | 廖宏霖 |
 |
參選組別: | 學生組 |
 |
參選項目: | 詩詞 |
 |
作品名稱: | 支離疏 |
 |
名 次: | 優選 |
 |
創作時間: | 97年4月30日 |
 |
作品欣賞: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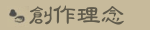
支離疏語出莊子的人間世篇,描述一個身形詭異的人物,一種殘缺不全的存有狀態,被人所歧視,更不被人所理解,但卻能夠在紛擾的世間安然自得。或許詩的語言也正是如此,晦澀、破碎、難以理解,無法被所有人接受,也從不是一種常態的語言,然而支離疏般詩的語言卻總是與自身溝通,彷彿不受形體所束縛,不臣服於文法和修辭。語言如果是一種思考的枷鎖,那麼詩語言的詭態、畸零、甚至造作就是鬆開思考、獲致自由的可能。(以上為創作理念) 這三首詩,第一首主要表達的是意義在語言中命定般的不完滿,即便是想像力也難以填補的缺口,詩因此無非就成為了一種撤離的狀態,不留給想像力任何的餘地。第二首詩談的則是聲音,詩的語言所保留的韻律與節奏就像是一種燃燒正常語言過後的一種灰燼般的狀態,也像是某種從隔壁房間所隱約傳來的不在場的聲音,詩從不描述聲音,它只展現聲音如同用它的身体與人交媾,人們透過詩獲得關於語言高潮的聲音。第三首詩所要表達的則是語言的無性生殖,如何從母體般不被切隔斷離的一次性敘述,分裂出兩個敘述的孿生兄弟,那些在句子斷裂處的重複彷彿一個個變形的節點,蓄積著語言被一再虛擲的張力。(以上為詩作註解)